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师琰 伦敦报道
唐宁街十号新住户苏纳克(Rishi Sunak)正挽起袖子,迅速扫除前任鲁莽政策引发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烂摊子,尽力提供市场相信的也是英国人曾引以为豪的“稳定”。但只有“稳定”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打破低增长魔咒。
一个新词已诞生,“英大利”(Britaly)。随着在50天里拥有第三位首相,英国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国家看起来像二战后内阁平均寿命约一年的意大利。有专栏作家调侃说,英国首相过去和葡萄酒一样,每隔几年就可能出一个经典;现在他们像水电费账单一样来来去去:痛苦,完全令人难忘。
不只是政治生态走向一致,在特拉斯“迷你预算”引发的金融混乱顶点,英国的五年期国债借贷成本甚至一度高于意大利。
连意大利前总理伦齐(Matteo Renzi)也惊呼:“无法想象有一天我们会出口最糟糕的‘意大利制造’——政治不稳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把它出口到了长期以来一直是民主和强大治理机构灯塔的英国。”他还感慨,特拉斯的45天任期惊人纪录“即使是意大利人也无法超越”。

(图为约翰·凯,受访者供图)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John Kay)最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认为,造成如今一切乱相的根源是传统政党结构趋于崩溃。不止英国,其它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情况也类似。对英国经济来说,迫在眉睫的是解决通胀问题,但通胀本质上是暂时的,更大的问题是,通胀究竟会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
74岁的约翰·凯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首任院长,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伦敦商学院教授,并为多个政府机构担任智囊,现任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誉研究员、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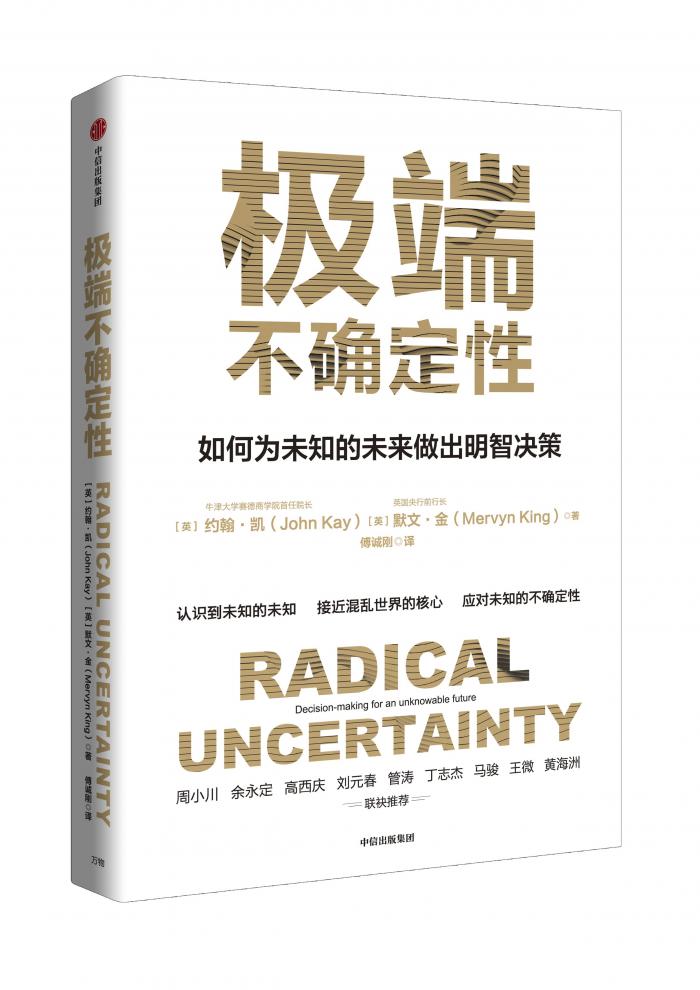
中信出版集团最近引入并出版了他与英国前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合著的《极端不确定性:如何为未知的未来做出明智决策》一书,他们在书中颠覆性地批判了引领过去数十年金融经济研究和宏观经济理论的主流思考范式,指出,在经济学主要领域一直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所有不确定性都可以定性为概率。这种信念是错误的,许多不确定性无法定性为概率。这种分析模式所依据的主观概率根本不存在。
在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量化预测反而更容易使决策者产生误判。正因为一整代宏观经济学家都忽视了极端不确定性无处不在,所谓计量经济模型和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时,才基本不起作用。
在这两位经济学家看来,现代金融经济学的三大支柱——有效投资组合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有效市场假说是有用且不可或缺的模型,但三者都没有将世界描述为“真实模样”。如果人们过于片面地理解这些金融模型,用人为创造或是取自历史的数据假设一种并不存在的静止世界,并据此做出重大决策,便如同刻舟求剑,这些模型将具有误导性甚至危险性,正如全球金融危机和许多其它例子一再证明的那样。
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时代,一个各种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的世界,无论对政策制定者、企业决策者还是个人,决策往往不是寻找“最优”解决方案,而是需要倾听更多声音,探寻究竟发生了什么,寻找限制条件下相对可行的方案,建立稳健性和复原力应对各种极端不确定性。
一个有趣的巧合是,这本著作2020年3月10日在英国首次发行,其中提到:“鼠疫不会卷土重来,因为它已经可以轻易被抗生素治愈,在发达国家中霍乱也几乎不可能大规模流行,但是,某种之前不存在的病毒有可能席卷全球,我们也要为此做好心理准备。”13天后,英国政府宣布全国封锁。
批评主流经济学误入歧途顺便成功预言了大流行的约翰·凯并不以为意,他举例说,这不是研究概率得出的结论,而是在以常识探讨可能性。
面对“未知的未知”,经济学主流研究手段误入歧途
《21世纪》:很多人都还记得,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金融海啸爆发后不久访问伦敦政经学院,在与教授们讨论经济形势时她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金融危机)?尴尬的现场没人能回答。
你和默文·金的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个解答吗——因为这些年来的经济学研究是走在错误的效仿自然科学的路上,没有正视极端不确定性其实无处不在?
约翰·凯:我认为,说没有人预测到事情严重失控,这既对又错。在银行和金融领域,很多人都很清楚。没有发生的是任何人可以预测到金融危机将在2008年9月爆发,因为这不是你可能拥有的知识,这与其它问题有关。
不仅如此,还有我们所说的,被认为是经济体系中的“反身性”理论(Reflexivity,首先市场总是表现出某种偏向;其次市场能够影响它预期的事件)。如果人们能够预测到2008年9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它就不会发生。这并不意味着说一些严重的状况不会发生,而是不会是以那样的形式。
当我们在书中谈论世界很可能会受到由未知病毒引起的大流行的影响时,新冠还不存在。你可以非常理智地谈论这种事情,但我们不可能说会有一场大流行病将在2020年爆发。谈论可能性和它会发生的概率不一样。
《21世纪》:你在书的开篇显著位置引用了哈耶克的话——我更喜欢虽不完美但正确的知识,而不是那种貌似精确但很可能错误的知识。
这是哈耶克在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说《知识的僭妄》里讲的。选用这段话是希望传递怎样的信息?
约翰·凯:我认为,哈耶克比很多人更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这段话也是对我们刚才所谈观点的印证,即你可以对一个事件有大致了解,但这并不等于能够以任何形式的准确性来调节或预测。
《21世纪》:哈耶克当年就曾批评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过于信奉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有可能招致令人悲哀的后果。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种思维范式和研究手段还是能成为主流?
约翰·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希望提出一种主张,认为经济学的科学地位是与物理学相当的。
第二个原因是,在当今学术界的工作方式中,你会被困于特定的发展路线。也就是说,为了让一篇文章在主要期刊发表,你必须符合一种标准模板。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两种标准模板,一种是相当抽象的模型,另一种是对非常庞大的数据集的分析。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在历史上很有价值地区分了关于科学探究的逻辑——世界的三种主要推理方式,即从溯因、演绎再到归纳法。皮尔斯认为,所有这三种推理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完整而动态的方法循环,以求获得科学知识进步。
但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演绎和归纳的方式。就像律师和历史学家在处理本质上独特的情况时通常喜欢用归纳法,他们需要找到一些特殊解释,使那里的数据有意义。而要理解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金融危机和大流行,我认为必须采取溯因法。
《21世纪》:你们呼吁经济学界改变对风险预测的态度和选择,不是考虑所有可能性并计算出其相对重要性,而是通过经验和判断。是否可以将这理解为让经济学和金融研究回归常识?
约翰·凯:嗯,这将取决于常识和常理。有些人的常识在过去经常得到正确的证明,而这是基于真实的经验和理解。也有一些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他们,比如我们的前首相或美国前总统,他们在没有什么依据的情况下表达强烈的意见。 因此,人们不应该只是说这是常识,而是应该为判断和经验留出更多的空间。
稳定事实上并不长期存在
《21世纪》:自俄乌冲突以来,一切都变了,现在相对和平和价格稳定的日子似乎已经远去,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应该如何驾驭这个充满挑战的新的全球环境?
约翰·凯: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我们说服自己,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市场经济和相对的政治稳定是适合所有地方的东西,并将在所有地方被采用。而我们在后来一系列事件中了解到,无论是2001年双子塔被炸毁,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或是像民粹主义政客的崛起,都让我们学会了对这种稳定性产生怀疑。
所以我不认为俄乌冲突是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只是开始确信:某种程度的稳定事实上并不长期存在。
《21世纪》:既然现代宏观经济模型不起作用,如果放弃概率推理和模型,经济政策决策和商业投资决策看起来就更像是一门对经验和判断力要求很高的手艺或艺术,如何确保和衡量决策者做出的是合理的决策,以避免损害公共或集体利益?
约翰·凯:找到稳健和有弹性的战略。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将能够调整政策,以观察和管理许多你无法完全预见的情况。
美联储加息抑通胀错了,有可能将世界拖入不必要的衰退
《21世纪》:你怎么看美联储现在的货币政策走向?斯蒂格利茨最近建议美联储应该静观其变,因为数据显示,通胀和通胀预期都有所缓和,美联储创造更高的失业率是不负责任的。在如此多的不确定性中,它应该暂停加息,直到对宏观经济状况有一个更可靠的评估。
约翰·凯:我认为这很有道理,因为有两件事正在发生。一是我们十多年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在系统中创造了太多的短期资产和通胀潜力。
其次,今年通货膨胀加速的事实几乎完全是由国际因素引起,它们是暂时的,我的意思是欧洲能源危机将得到解决,全球食品供应问题在一、两年内也会得到解决。
因此,我们应该拭目以待,看看核心通胀率在多大程度上会被逆转。我们不妨把这些特定价格变化的影响剥离出去,观察核心通胀率发生了什么,人们的通胀预期是否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21世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联储应对两位数通胀的行动引发拉丁美洲债务危机;2010年代,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又扰乱了巴西、印度、印尼、南非等国经济。这一轮紧缩被认为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你是否担心会引发另一场亚洲金融危机或再度让拉美国家陷入挣扎?
约翰·凯:这的确很有可能。我认为,美联储或任何其它中央银行相信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微调通货膨胀率的想法是一个错误。央行通过明显地提高利率,对公司和国家造成很大的干扰。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和观察,不急于做任何决定的策略是非常有意义的。
《21世纪》:全球加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生,这对它们各自的国家来说或许是可取的,但这些行动的叠加累积影响可能比预期的要大,是否可能将世界经济拖入不必要的衰退?
约翰·凯: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应急于求成。几十年来中央银行的普遍独立地位使人们相信,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微调通货膨胀率,而我不相信他们可以做到。
《21世纪》:自去年以来,欧洲能源消费价格已经上涨了45%,这让许多政治家相信,除了大规模国家干预,别无选择。由于匆忙制定的措施,政府不得不为飙升的能源账单提供大部分补贴。你认为欧盟在欧洲能源危机下的政策应对如何?
约翰·凯:我不是能源政策方面的专家,但这涉及到我们该如何处理极端不确定性。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建立稳健性和复原力。这就是说,由于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具体细节,我们必须采取稳健和有弹性的战略,以应对无法预料的事件。
这里发生的事情是,特别是德国采取的能源政策并不稳健和有弹性,而且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我希望这个教训能被接受。
更广泛的是,新冠大流行和所有因此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希望也会让企业意识到需要采取比过去更稳健和有弹性的商业战略。
《21世纪》:最后,你能否总结一下你希望让中国读者了解的核心观点。在一个极端不确定的世界里,个人投资者如何面对动荡?到底什么是理性的反应?
约翰·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多样化的问题。我们不能总是对人们说,管理投资组合的风险就是要实现多样化,倒不如找一些知道你应该做什么的人,如果有人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你应该非常仔细地考虑考虑这个主张。
我们一再谈到的理性反应是稳健性和复原力,这是这个战略的关键要素。我在谈到极端不确定性时,往往以找到管理风险的策略来结束,这样你就可以拥抱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往往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需要应对风险虽有弊端,但这样你不仅可以与不确定性相处,甚至欢迎它为你提供的机会,否则可能根本无法获得机会。



















